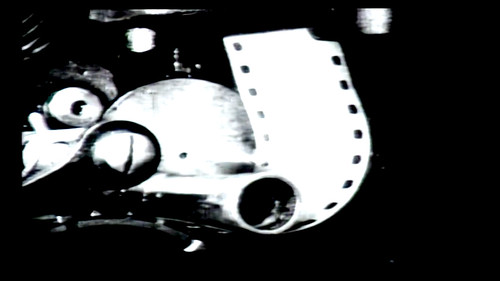【C-LAB影展】高達《影像之書》:老野狼的懺悔

「每個人都想當國王,沒有人想當浮士德。」「這部片要說的是正在發生的事,或者說沒發生的事。大多數的電影,尤其像是今年坎城競賽的電影,描述了事情的發生;但多數的電影沒說的是『沒發生的事情』。」
──高達,《影像之書》坎城影展記者會
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已經 87 歲了,他幾乎是最後幾位碩果僅存的新浪潮大師。2018 年 5 月 12 日,《影像之書》(Le Livre d'image)於坎城影展首映後,隱居瑞士的高達,透過 FaceTime 軟體中介,以手機屏幕上的現身取代其肉身,睽違多年後重回坎城參加媒體發布會。
他說,我們用腦袋想了太多事,但是沒有用手做的事太多了。
延續《電影社會主義》(Film Socialisme,2010)、《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1988-1998)的形式與精神,《影像之書》是一部五個章節的電影。高達說,一部五章節的電影,正如一隻手的五根手指。前兩章「Remakes」、「St. Petersburg’s Evenings」,從電影史切入,探問製造戰爭的法律、政府、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後半段「These flowers between the rails, in the confused wind of the journeys」(此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詩句)、「The Spirit of the Laws」(法意)、「La région centrale」,通過孟德斯鳩《法意》的書名,深入正義的本質,轉而批判媒體中去人性的阿拉伯形象,進入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考古。
記者會上,高達說:「這不是政治電影。」他說:伊朗、敘利亞、巴勒斯坦,中東的篇幅僅僅只是呈現了阿拉伯人的生活,快樂的阿拉伯人──他在其他人的電影中,從未見到的一切。
然而最後一個章節結束時,高達又斷然表示:「你們甚麼都沒看到」──儘管如此,他繼續不停地說。
高達在《影像之書》中一直在「說」,這是他的生死之書。明確意識到生命的極限,他在電影裡以蒼老的聲音、時日無多的老者姿態,告誡世人「沒有用手做的事太多了」。與尼可拉溫丁黑芬(Nicolas Winding Refn)在《罪無可赦》(Only God Forgives,2013)中對手的迷戀相仿,高達卻沒有以「斬手」儀式,來制止自己向來膨脹的創作者靈魂。
高達在一篇訪談中「說」道:《影像之書》對他來說就像是一本圖像書,影像本身甚麼都不會說,甚麼意義都沒有。但透過影像(image)的堆疊,蒙太奇的組合,影像成為了「說」(speech),卻還不是語言(language)。 所以電影中這麼說:「關於這個世界,我們說的永遠還不夠。」(We never speak enough for the world)高達在記者會中提及,音畫分離,讓聲音和影像可以形成真正的對話和共鳴。或許這就是高達在第一章,對電影、電影史、好萊塢電影提出質疑時,對「電影是甚麼?」這樣的老問題,所提出的解方:透過剪輯(他說,就算是數位剪輯,還是得動手,五隻手指一起),聲音和影像,誰也不箝制誰。
這是一部「低技術」的影像詩。高達拼接無數老片影像,他分離檔案影像的音軌,造成音畫錯位,從此影像兀自漫遊在變形的比例,他還讓字幕、旁白、影像聲音各說各話,用顫動的畫面、抽格的色彩來進行諷刺;甚至大玩八聲道音響,讓雜訊感(glitchy)疏離知覺,極盡蒙太奇之能事。透過這些吟詠,論證文明的必然罪惡,亦即我們的文明是仰賴戰爭的文明,從法律到政府,論證、控訴的戰爭、虛偽的政治、形同虛設的政府,黑暗、黑暗、黑暗……蒼老的聲音不尋找希望,只有絕望。
儘管如此,高達在電影開頭,以達文西《施洗者聖約翰》的手開宗明義表明:影像無關「抱負」,無關資本,無關勇氣,而只關乎「實踐」,用手做事,「登上歷史的列車」。當五個章節,以班雅明式的排列(Constellation),像五顆星星一樣,兀自陣列而出:一個星座指向了最後的一個章節。高達在訪談中說,那是一隻「手」。最後的章節中,高達堅守老左派風格,從杜甫仁科(Alexander Dovzhenko)《土地》(Zemlya,1930)中的一對戀人的面孔出發,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盧米埃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的影像中,一次次地,他用蒼老低沉的嗓音無力地嘶吼。他相信「革命」,但他說當今的人們「都只想當國王,沒人想當浮士德。」
聲嘶力竭的控訴,一隻手指向著黑暗,四隻手指更向著自己,原來這是懺情錄,剛剛的各種攻擊、詆毀,都是自剖懺情的藥引。他用各種層次的粗糙質感,躲藏在資料影像後的懷疑主義式碎碎念,在記者會高談闊論影像哲學;然而,當他幾近憤恨地召喚 ISIS 屠殺影片和「東方主義」想像,大問西方中心主義者:「你們憑什麼決定他們的幸福?他們需要你的幫忙嗎?你知道他們要什麼嗎?」他像是個影像的土製炸彈客,以一雙無力的雙手,在剪接台上敲擊出嗓音,僅僅只是聲音,不是論述,更不是語言。漫無目的,像鬼魂,他的魂魄漫遊在政治、哲學、電影史中,他說:這些都只是文字,文字的堆疊終究不會變成語言。
他說:沒有真正的革命。
坎城記者會中,高達說,現在的他以另外一種方式思考電影:「X+3=1」,X 是負二,X 是電影。高達說當今要拍出好電影的關鍵(key),一幅好的幀格,倚賴的是前後兩幅被捨去的畫面。電影影像為了呈現「現實」,得削減「過去」、「未來」,因此電影是負二。高達也提醒我們,既然是鑰匙(key),就不能忘記那個鎖(lock)。
高達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口中,害「藝術已走到終點」的藝術家,卻也是大衛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心目中,開創電影第三條路的希望。如今,坎城影展的記者會上,當年的野心與洞見仍在,同樣的虛無和尖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電影的極限,他站在語言的前緣,無聲地呼喊。諷刺的是,他的姿態讓他跟他批評的人並無二致。
記者會尾聲,主持人告訴他,在記者室角落的陰影中,有他當年的學生要跟他打招呼;高達說他記得,當年在巴黎的咖啡廳,兩隻小綿羊乖乖地聽他這隻老野狼說話。記者會結束時,高達俏皮地說:「大野狼要跟你們說再見了」,眾小綿羊們鼓掌。高達的電影是難懂的,他像是大野狼,一次次威脅溫順的綿羊們,但狼來了的故事到了終了,仍然沒人學會教訓。即便如此,他還是在那條未見終點的路,繼續走著,偽善懺情也好,聲嘶力竭也罷,至少他的手跟腳沒有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