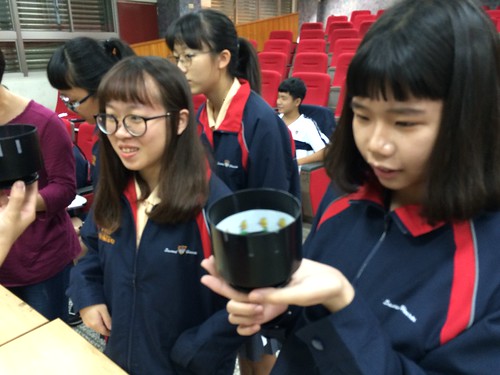文化理解?或藝術品味?青少年電影課的反思
冷彬,富邦文教基金會的總幹事1。當她身懷六甲出現眼前時,本擔心訪談時間需謹慎精簡拿捏,無法盡情延伸提問。未料她興致高昂,滔滔不絕,從個人興趣、基金會定位、青少年培力、電影學校,到針對臺灣教育體制等等問題,暢談三小時欲罷不能。
外貌清麗亮眼,談吐條理自信的冷彬,曾因收藏史努比走紅,撰寫過《我們的史努比收藏》(2002)、《愛上史努比》(2003)等書。從她一再提到對自己收藏觀點的「嚴厲自我反思」,即可窺知其強烈的自我覺察意識與批判能力。於是我們的史努比話匣子暖場未久,她就迅速俐落地將談話切入關注主題──青少年影像教育。
2014年開始,基金會規劃執行了許多青少年影像教育的活動。從法國電影教育作為學習範本起始,再一路挺進到臺灣各鄉市鎮學校,並與影展、博物館等單位機構合作開設各種電影課程與工作坊。今(2018)年7月,更將這四年來累積的研究資料與實務經驗集結成書──《迴映誌:影像年代下的教育現場》2,顯示出近年影像教育在國內外等公眾機構蓬勃發展的趨勢,亦可提供作為臺灣未來政策探討與教育推展的文本基礎。
為什麼是青少年?
令人好奇的是,回歸基本核心來看,究竟為什麼是「青少年」?青少年是如何被設定出來的族群?一個財團文教基金會又為何要推動電影學校的計畫?冷彬先從自身經歷說起,「我人生幾乎都在跟青少年互動」,社工專業背景的她──台大社會系社工組畢業、取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工系碩士後,返臺進入基金會工作,一直都在與「青少年」這個特殊族群做溝通對話。因為出國唸書的經驗,也讓她觀察到,臺灣的青少年相對國外青少年來說,有一種集體性的延緩發展,當然這可能源自於臺灣的升學主義導向。她隨即感嘆:「我認為,造成臺灣現在沒有核心價值的主因,就是因為很多掌權的大人在青少年階段的問題沒有處理好。」比方認同感、好奇心、同理心、文化素養等基礎能力,如果青少年時期沒有建構完成,未來也很難培養。所以相較於高年齡層,「你投入5年、10年去教小孩還是比較有希望啦!」冷彬笑說。
|
文教基金會的主要工作,就是透過各種教育活動達到「青少年培力」的目標──讓青少年主體的內在力量發揮出來。
|
基金會1990年成立之時,即已設定主要對象為青少年,推動媒體素養教育與相關活動。由於執行董事陳藹玲具備媒體工作背景,夫婿則是富邦集團的大董蔡明忠,「他們理解教育的價值,有一種非常純粹的信念」,總是批判力道極強的冷彬,語氣頓時柔軟了起來。她認為,臺灣集體對於企業責任的概念,基本上仍是以急難救助為主,「偏偏教育無法速成、求不了什麼光環、更沒辦法給漂亮的數據。」幸好富邦集團旗下有各種不同基金會,彼此可在不同領域各擅其場。因此文教基金會的主要工作,就是透過各種教育活動達到「青少年培力」(Youth Empowerment)的目標──讓青少年主體的內在力量發揮出來。
影像教育在國小、中學與大學的不同
近期基金會影像教育的對象也逐漸擴展向國小,亦即延伸「兒童」族群為目標。以臺灣現行學制的國小、國高中、大學細分來看,由於大環境少子化的關係,國小校方與老師都有意願朝向特色課程發展,所以現正著手開發適合這年齡層的教材,「國小教材跟高中職完全不同,雖然必需重新開發製作,但基本上國小的問題不大。國中才是真正的黑洞!」冷彬無奈搖頭,似乎也無法對抗現今升學體制與家長期望的多重壓力,「國中的學科考試導向,導致電影教育幾乎無法介入。」
|
由於「觀看經驗狹窄、生活經驗封閉與課業壓力下,他們很難用創作去說自己的觀點」――因此,青少年影像教育的重點便試圖回應「觀看」這件事。
|
至於大學面臨的狀況又跟國中生不同,「大學生很希望快速有作品產出,可以參加大小影展獲得機會資源,進而朝向電影產業工作發展。」這樣的心態造成創作思維與能力較無法緩慢累積。如果說,現今臺灣生產出的劇本或作品經常類型單一、故事貧乏,「我認為就是源頭養成出了很大的問題」,冷彬毫不留情地批評。所以相對而言,她認為高中生比較沒有這種速成的壓力,於是一開始是先帶著高中生從事影像創作,但發現由於「觀看經驗狹窄、生活經驗封閉與課業壓力下,他們很難用創作去說自己的觀點」──因此,青少年影像教育的重點便試圖回應「觀看」這件事;加上近年高中課綱鬆綁與大考趨勢的改變,促使高中校方也願意接受多樣性的課程內容──雖然這也算是考試領導教學的結果,不過高中生的確比較能夠透過看電影的學習過程,慢慢培養認識自己與觀察社會的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2015年基金會正式與國家電影中心合作,以高中職學生為主要對象,推動「全國高中職巡迴電影學校」計畫,瞄準了現行高中教育體制裡的空缺,發展出一套透過觀影建立的學習系統。
「現場」累積實戰經驗
那麼,新計畫如何落實到臺灣現行的教育體制呢?基金會一方面翻譯法國電影教材、也編寫原創的本土教材;另方面則實際大量進入學校田野工作,介入包括多元選修、「藝術與生活」必修、主科(例如國、英、社會)協作必修等課程型態。每週2小時,每班學生人數20-80,藉由不同學科需求,搭配專業講師導讀、觀賞、討論影片。
在教學過程中,基金會則扮演了溝通合作的重要角色,「絕不是直接給資源就好」,冷彬解釋,「我們一直在『現場』,持續累積大量對學生的觀察,這在台灣很重要。」因為無論是校務行政或學校老師,起初一定提出許多質疑,尤其老師經常用「你們不懂現場」來做回絕,比如課堂上必需管理學生秩序、張羅各種事情等等理由,「但我本身就是前線訓練出來的青少年工作者,所以每個案子一定會安排基金會的人在現場!」
|
從這些經驗值跟老師互動,他們覺得你努力過,不是用想像力、一廂情願開發你認為重要的教材。
|
透過三年來約45間學校、50名合作教師、1500名學生所累積的實際經驗,「從這些經驗值跟老師互動,他們覺得你努力過,不是用想像力、一廂情願開發你認為重要的教材。」冷彬舉例,之前就曾經因為「選片」問題與學校發生爭執,鄉鎮學校認為某部影片只適合城市學校,不適合他們鄉鎮孩子,「完全低估了學生的能耐!」於是基金會團隊也因此細緻地將學校現場分類,每場都有工作人員親自前往不同層級的鄉市鎮,在明星高中、社區高中、綜合高中、高職等不同學校反覆演練與實驗,逐步從成功與失敗的案例裡獲得繼續推進的基礎。
冷彬不諱言,這麼大量的實驗教育經驗,正是民間團體的彈性與動能,「我們有人力、時間,到不同的鄉市鎮學校,面對不同的學生類型,再評估教材對他們的不同影響。」最終希望這些教學經驗、教案素材都回饋給學校裡的老師,開啟學生思考進步的可能性。
青少年影像經驗的根源問題:網路媒體
針對青少年影像教育的城鄉差距問題,冷彬則解釋:「某些片子在臺北學校可以運作、在其他地方不行,並不是因為孩子是否具備都市經驗,而是根據他觀看電影的經驗與累積量。」比方說,鄉鎮孩子可能有更多時間看各式各樣的電影,「因為他在家就開著電視的電影台,一直看、一直看,看很多老電影。」所以電影作為一種教育載體,跟傳統課業上的教育資源城鄉差距是不一樣的。
現今提倡的「翻轉教育」,主要就是透過網路來傳遞影像教學素材,試圖解決城鄉之間的教育資源差距。「這當然是很大的進步,但這些便利性,都還是在處理學業能力。」冷彬聲調拔高地說:「現今城市、鄉村、部落的青少年都人手一機了,觀看的都是一樣的網紅、影像媒體!」因此她認為臺灣影像教育的根本問題,跟學科的城鄉資源差距並不相同,真正問題是根植在網路媒體的影響,「城市與偏鄉孩子的觀影內容愈趨於同質性,基礎地改變了孩子認知的狀態,這是非常巨大的危機,沒有人談論這件事!」
|
城市與偏鄉孩子的觀影內容愈趨於同質性,基礎地改變了孩子認知的狀態,這是非常巨大的危機。
|
因為網路影像,造成全世界青少年的心理、情緒、偏差行為等問題愈來愈趨向同質,反而愈少源於種族、國族、區域等傳統認知的差距。冷彬犀利指出:「臺灣偏鄉孩子他們不缺硬體、而是軟體,缺乏有意識地跟他們討論這些事。」比方身為原住民孩子一直觀看不屬於自己文化的影像,同時也無法思考如何將自己的原住民文化影像傳遞出去。
當多樣性、異質性被網路科技稀釋,青少年觀看的影像內容愈來愈一致,我們該用什麼方法帶孩子去回應處理?冷彬批判說道:「我曾經去挑戰那些『翻轉教育』的老師,為什麼你們完全是在『學業導向』裡翻轉,強調培養全世界最好的數學、科技、創新人才……?你們是不是應該更加培養孩子們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感?」由於孩子們長期觀看來自中國或國外的網紅及網路短片,個人與集體的認同正快速改變,「我們台灣到底有哪些東西是希望孩子們認同的?又如何從台灣來認識與理解更寬廣的世界?──我非常、非常擔憂這件事。」
但臺灣對於這方面的學術研究非常少,現今主要處理的還是「翻轉教育」藉由網路方式提供孩子自主學習的「課業」議題。然而「網路世代」改變了速度、時間感、文化認同,以及青少年影像觀看的同質性卻少有研究。「我很擔憂,究竟在國民教育的階段,我們要把孩子變成什麼樣的一個公民?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就會變成一個全面性、也是更關鍵的問題。」
藝術課?或通識課?──臺灣電影教育面臨的挑戰
如果依照培養「公民力」的邏輯,電影學校師法法國的方法,在臺灣面臨很大的挑戰?「從大結構政策面來看,現今文化部長對國家電影中心相對重視,所以影像教育在政策推展上,是有所提升,」冷彬分析:「不過在臺灣的教育系統裡,把電影置於『藝術與生活』課程、而非『文化養成』的思考,這是我看到臺灣與國外經驗最大的落差。」
法國的國家電影中心(CNC)、博物館、各地學校等,對於影像教育推廣不遺餘力,投入非常多的經費開發教學資源。所以在定義上,法國視電影為年輕人的基礎教育,「你把電影看成是『文化』、或『藝術品味』,完全是兩碼子事!」
|
你把電影看成是『文化』、或『藝術品味』,完全是兩碼子事!
|
兩種截然不同的定義,即會生產出兩個不同的應對方式。冷彬強調她多年的觀察,「台灣教育部把電影教育放在『藝術與生活』是完全行不通的!時數少,又要跟視覺藝術、音樂、美術等爭搶資源,文化養成如果只是成為一禮拜2小時的時間,那是非常荒謬的事!」當電影被視為休閒娛樂、附庸風雅的藝術喜好時,它就會不斷被邊緣化,「我現在不太喜歡從藝術學科來談論電影學校,因為當你硬用學科來談論電影時,相對於國英數理科目等,電影就變成次要的。」
而文化素養是一種基礎能力。如果從「文化」角度看待任何一種藝術形態,比如電影就會置於在「人」的脈絡裡──成為一位公民所具備的基礎素養能力。身為一位公民必需擁有自己的想法,參與、理解、認同自身的文化,「所以電影識讀是公民養成的一部分,不是喜好!它在臺灣教育系統裡更應歸屬於『通識』課程。」
然而無論是電影美學或文化素養,老師又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長年來,臺灣老師們極少從教育體制裡,學習理解電影歷史或電影語言,而文化素養又非一蹴可幾。「教育太現實了,它就是人跟人。雖然網路也是一個方法,但重點還是老師」,冷彬斬釘截鐵地說,「你教批判思考、你自己就得有批判思考;你教文化素養、你自己就得有文化素養,以及同理心等等都是。」批判能力與文化素養等基礎能力,都難以規範出一種教學方法,它很仰賴老師自身特質,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自我覺察、對人的敏感度、意識到位置與權力關係等,「這些都是沒有捷徑路線的!」
在影展與博物館場域延續公民文化教育
延伸出學校體制的現場,近期青少年影像教育活動也拓展到影展與博物館,例如與紀錄片影展、臺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等推動「青少年評審團」的相關活動。透過課程講述、評片討論、文字寫作等方式,培訓對電影有熱情的高中生。這樣的學習模式與學校的教學邏輯系統有何不同嗎?「我認為,青少年評審團並不需要安排很多的講座,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思考、討論!」
冷彬依然從其大量的田野經驗來說明,因為影展召喚來的對象與學校不同,他們會更需要訓練強化思考表達能力,而非長時間聆聽電影課程。「比方我們希望安排同學去訪問導演,如果影展單位給予這個機會,我們就會去創造一個教育學習的歷程,培訓準備好這些孩子。」
|
你可以改變立場,但不能無話可說。這是我們跟孩子工作的邏輯。
|
「所有的教案設計的最後,我們都會要求同學們拍片、寫作、或任何一種形式的實作成果。」成果即使很小,也需要練習;因為人不可能毫無意見,也不可能永遠秉持中立,「你可以改變立場,但不能無話可說。這是我們跟孩子工作的邏輯。」冷彬話鋒一轉,談起跨領域之間溝通合作的重要性,「關於教學目標、老師選擇、課程的節奏等等細節,這些都會需要與影展單位反覆溝通。」因為影展單位擁有電影資源,基金會具備許多教學現場經驗,兩方需要建立足夠的信任關係才能夠順利工作。
「教學現場畢竟是我們的專業」,冷彬再次強調現場的重要性,「我發現學生出了狀況,你們必需尊重我的判斷,一起幫忙處理問題。」當然這要一直反覆溝通與磨合,「如果真心希望孩子成長,我們都會需要很多的信賴與耐性,才能夠跨越現有的本位困境。」冷彬同時提到:「紀錄片影展就是很好的合作例子,他們非常清楚意識到你講的都是思考過的;即使不完全理解,他們也很願意動員影展資源、提供素材,對應我們對影像教育的期待。」
|
▍延伸閱讀
570期【放映頭條】
|
另外在博物館的場域,基金會也投入開設青少年影像課程及工作坊,例如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史前博物館、臺灣歷史博物館、人權博物館等。透過轉化博物館各式各樣的素材,成為可以親近、認同、連結生活成長經驗的教育的可能性,「這些都需要花力氣的,也需要不同的專業工作者,一起工作。」
冷彬最後一臉認真,「我性格比較務實啦,我相信大家彼此溝通合作還是有機會改變現況。」她強調,台灣當代社會已經沒有太多可以對立撕裂的條件,當大部分人可以過小確幸生活,極端抗爭是難以施力的;而社會集體沒有核心價值,也難用價值來溝通。那麼,大家最終可以妥協的交集在那裡呢?「就是對這個社會的認同,一個文化的主體性。」
小結
從頭仔細來看,顯然在冷彬的思維裡,「青少年」才是她最關注的主體焦點。電影教育、媒體識讀、文化素養等等都是圍繞此核心所幅射出來的領域。她從社工、社會學的方法論,以大量實證經驗做結構性的系統歸因,試圖解決臺灣當代青少年正面臨的影像觀看困境。
「我們努力反覆實驗做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回饋給體制裡的老師,因為他們才是真正面對可能成為問題孩子的第一線。」腦中持續迴盪冷彬這段話。
如果把集團企業「投資」電影學校與文化教育的這一切,都歸究於資本主義的商業心眼,實在是再容易不過的簡單邏輯。然而無法否認地,也正如冷彬在訪談時曾說:「再糟糕的學生都可以辨識出來誰是好老師、誰是壞老師!誰是真心為他們好。」因此即使自身原本眼光邪惡,但近身聆聽大量熱切的經驗分享與理念闡述,的確可以輕易辨識出,有一群人對臺灣青少年教育的積極投入付出及真心純粹善念。
三小時的青少年電影課,一趟充滿反思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