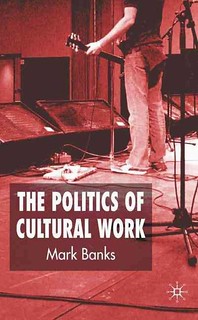從紀錄片工會的組織想像團結
2016年,台北電影節將「卓越貢獻獎」頒給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紀工會),除了肯定工會積極出版相關訪談論述、建立歷史觀點,也對提升整體影視產業的勞動環境、權益維護起了相當正面的效果。
2006年9月9日,紀工會由一批以導演為主的紀錄片工作者成立,包括楊力州、蔡崇隆、顏蘭權、黃信堯等,並定調了以「勞動者」為主體,再擴及技術人員、電影相關行政行銷人員,提供勞健保投保、勞動契約簽訂、版權放映費用等諮詢。後續,面向會員以外的一般群眾,也創辦了紀工聚會的交流平台,並以報導文字累積資料的紀工報,乃至書籍出版品。目前紀工會會員人數約480人,一年繳納會費1800元,九位理事、三位監事,下設秘書處聘請四位專職員工,規劃經營各種工會活動。然而,編制雖小,經費短缺時秘書處及幹部仍須透過接案,與各企業機構單位合作,以賺取足夠的營運經費。
此前,產業內的組織多為聯誼交流、承攬活動為主的各種協會、學會,而其他職業工會(如台北市電影電視演藝業職業工會)則以提供投保勞健保為主。而當2006年紀工會成立,喊出:「其實我們是勞工!」的口號,也是認了勞工身分,重新摸索自己所處勞動結構,並意識到各種關於勞動彈性化、薪資級距、權益、版稅分配等問題的開端。紀工會理事林木材說,多數紀錄片工作者都沒有固定雇主,也沒有保險,而面對不同雇主,勞動條件往往差異甚大。根據筆者從幾位年輕工作者口中聽到的現實,也確實各自曲折:
案例A:不支薪的勞動
世新廣電研究所畢業的C君(化名),自學生時期拍攝畢業製作,從導演組場記做起,後來開始擔任製片,也試圖把製片工作當成專長,主要以獨立製片、公視「學生劇展」為主。由於學生製作費用由導演自籌,預算捉襟見肘,只能花在演員,前製及拍攝期的場地租借、交通及食宿,以及後期剪接、配樂、調光、混音等等。預算有限之下,製片的考量是把錢花在刀口上,盡量壓抑薪資,以多數學生劇組的情況而言,攝影、燈光、收音等技術組的頭可能會請系外朋友或已開始接案的free-lancer擔任,若有多餘預算,也會先將錢花在這些人身上。劇組助理由學弟妹、同儕組成,性質類似實習,基本上完全不支薪,頂多會在殺青後領到兩千元(甚至更低)的紅包,大家抱著「我不是來工作賺錢,是來學習、幫助導演完成作品」的想法。無論有無支薪,一般不會簽訂契約,僅透過討論協商,憑著人際關係情誼來解決問題,達到目標。
就「學習」而言,學校教授美學觀念與理論思考,實務操作則由學生各組團隊實際操練,一路各憑本事或運氣,嗑嗑碰碰。學生在實做中更加認識自己的能力、興趣、增加歷練或人脈,或因此得到更多機會或名聲,謂之「學習」。在這樣以學習、創作為主的思維下,是否應該計算合理的勞動報酬,便被排擠至不重要的階序。無償勞動以藝術創作或學習之名,被層層包裹了起來,但因為「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也無法追究任何人。C君說,因為人情壓力,互相幫忙也是互相欠債,幫完這次,未來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繼續鋪路,「有時候這樣的人情就是得硬著頭皮去還,無論拍攝狀況多硬薪資待遇多低都很難拒絕。」
案例B:層層剝削與過勞擠壓
如果這是學生製作的常態,業界新人菜鳥又會遇到什麼狀況?
1991年生,傳播系畢業的依依(化名)在學校裡受到的是觀念理論訓練;拍攝相關的技術操作則由學長姊私下教授,或透過網路知識、人脈、各種工作坊,摸索自學。畢業後,依依進入業界,想判斷這個環境適不適合自己,再決定要繼續升學或留在工作崗位上打拼。他大學時擔任過紀錄片實習生,畢業後進入電影劇組,擔任製片助理,與製片方簽訂兩個月合約,規定工時、工作範疇與項目,每月薪資25k且不含勞健保。但依依說,實際薪資其實僅22k,「我去找會計,但他的解釋我也聽不太懂。我自行投保勞保,每個月還要多負擔三千塊左右。」薪資含稅與否,往往是菜鳥被剝削的第一層,而合約規範則從確保製片方掌握著作權益、確保工作者不會拍到一半不幹,到確保班表以外的三餐交通全由工作者自理。
電視、電影劇組助理通常算月薪,卻是工時吃到飽的責任制,除了月薪或以案計價,另一種技術組、廣告、MV常見的方式是以班計算,一天24小時切割為「8664」,第一班為8小時,超時算第二班6小時,薪資每班價錢相同,以此類推。普遍情況是「跳班」,即連續工作,「跳三班」意指連續工作20個小時。以依依的製片助理工作而言,是月薪吃到飽,翻班(整夜工作到隔天早上)後儘管有休假,但休假期間因為過勞,只能倒頭大睡,或者被派去借器材、學開3噸半卡車或9人巴士(運送道具人員的劇組愛用車)、移動到下個拍攝地點,無形中剝削了工作者應有的休假時間。持續拍攝六天到八天後,通常會有一天休假,然而因為預算、天氣、拍攝時程等種種複雜因素,長達兩週才有休假,也是業內常態。
依依擔任的製片助理,即是一個被認為沒有門檻,只要足夠抗壓吃苦耐勞、被當成狗使喚的,劇組中最菜的新人。「製片組負責照顧、溝通、處理各種突發狀況,因此通常都要最早到、最晚離開,超過班表一、兩個小時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一天起碼需要工作14、15個小時,常常凌晨4、5點就要起來訂早餐,工作直到深夜12點。」依依不諱言,曾在身心狀況不佳的時候精神耗弱,甚至送醫急救,然而這一切並非僅只能夠歸因於「不耐操」、「草莓」,而是與結構中的極度擠壓與自我成就感不足有關。比如,他曾經覺得薪水太低向製片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你只值這個價格,還有人比你更低。」也被要求過去剝削別人,「因為casting組不願意找800元以下的臨演,而製片認為太貴,就要求我去找車馬費500元的臨演。」(指的是不管在現場待多久,只有500元「微薄心意」)。然而我們也都知道,這並非是製片是壞人,而是整體預算不足、持續往下cost down,結構中的弱弱相殘令人深感無力。
拍一部電影,每一天的劇組薪資、食宿費用都是一筆筆驚人開銷。回顧過去幾年,《海角七號》後出現許多製作費五千萬台幣以上、甚至過億的中上型製作,國片市佔率一度提升至17%。然而,2013年後國片市佔率達13.96%後持續低迷,成長停滯,2014年國片市佔率10.2%。近兩年製作預算下降至平均3000萬,甚至更低,直接衝擊到2010年左右入行的這批年輕人。假設一部電影預算大餅分三份,一份支付演員酬勞,一份支付場地器材,一份支付劇組人事,可推知若非降低人數,便是一人當多人用。
我問依依,還會想待在影視產業內嗎?他說,雖然仍在努力嘗試,但已經明顯感覺到身體變差,因為爆肝熬夜、過勞、只睡兩三個小時是常態,暴斃的例子在圈內時有所聞,也因壓力大,菸酒檳榔維士比都是業內常見的依賴,身體普遍不健康,若隨著年紀增長體力不支,自然無法繼續承受這種勞動強度。「以前我都覺得我很有熱情幹勁,沒簽約也覺得隨便啦!反正就做啊!不管自己墊了多少錢也沒關係,也不會計較爆肝,覺得反正我還年輕啊!」依依嘆了口氣說:「真的好天真,但我不是不想拍……」
部分影視產業工作者如燈光組、攝影組、場務組、電工技術人員,適用《勞基法》第84-1條,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合意調整工時與休假,但不代表工時可無限上綱。即使有一日連同延長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四週不得超過288小時的規定,仍沒有足夠約束力,長期被批評為「奴工條款」。若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訴,又因不夠了解法規權益、舉證困難、擔心接不到案子等問題而有諸多窒礙難行之處。過去發生過惡質資方拍完片就落跑,逼得被欠款的勞工尋求勞資調解的案例。依依便說:「就算法規改了有用嗎?大多數從業人員都是free-lancer,必須靠人脈維持案源,像妓女一樣一直接,如果停下來就會失業,起來抵制也會擔心自己拿不到案子。」
法令規定不明確,勞動者不夠清楚自己的權益,使得模糊地帶成為剝削溫床;然而,放回台灣的職場文化,卻又是內化至深處的自我剝削。此前不久,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美國獨立製片《沉默》來台拍攝,製作人溫克勒(Irwin Winkler)直言,正因為依賴台灣便宜的勞動力而能夠在有限預算內完成,引起業內朋友們一片譁然,也重新審視自己的勞動處境。如果繼續保持「沉默」,只會讓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殺人結構持續運轉,「我一直很期待大家什麼時候才會願意罷工?我也不知道工會為我做過什麼事。」依依說。
案例C:創作還是勞動?
面對各種真實的剝削與彈性勞動,團結組織會是出路嗎?阿方(化名)說「有這種意識,說不定會被罵」,如果提出問題,可能會得到「學長也是這樣過來的」、「年輕人太草莓」、「不爽不要做」、「撐住就是你的」、「不要靠北靠母」等回應。然而打開臉書「靠北影視」粉絲專頁,排山倒海的發文全是怨氣,在匿名的保護下說出了真話。常看「靠北影視」紓解負能量,現年34歲、非科班出身的阿方放棄繼續升學,轉向戲劇創作、進入影視產業,從電視劇製片助理及場記做起。「我的腦袋比較分析性,大概知道問題在哪裡。」阿方認為,台灣的結構性問題有二,主要在於文化層面:一是台灣長期反共,造成工會風氣不興盛,或早期成立的工會被國民黨滲透;二是儒家文化造成圈內的家父長制主宰一切體系運作,而教育的差異讓台灣人普遍缺乏分析思辨的能力,只能跟著混亂的生態隨波逐流。「雖然有極少數劇組不超班,工作人員都可以睡飽,比如說侯導,但只是他個人,不是結構性的改變。」
阿方在電視、電影、戲劇圈子都待過,「功能」也相當多元,擔任過道具助理、導演助理,一路上遇過不少的問題,也不乏被騙的經驗,舉凡付款太晚、自己吃下開車超速罰單、撞到道具器材或車輛付出上萬賠款、過度疲勞開車開到睡著、擔任電視劇助導整整一個半月沒有休假,或是原本已進入前製期,最後卻沒有開拍,等於白忙了幾個月……。因此,他轉而認清自己的優缺點,試圖在夾縫中生存,企圖透過編劇、創作的能力,等待機會打開另一扇門。
在文化勞動結構中,正由於這種廣義可被歸為藝術創作的工作,包含著某種無法量化的特徵,認定創作關連到自我實現,這樣的想法反倒使他們自我規訓、剝削自己,也正中資本主義的治理術視角。班克斯(Mark Banks)《文化工作的政治》一書便說:「通過自身持續性的回應努力,去支持、轉變或交涉工作場所中的進取式價值,由此『自發地』促成了權力關係的再生產。儘管進取式價值似乎會傷害文化工作者的利益,但弔詭的是,工作者卻把壓制他們的進取式文化,視為他們能獲得有意義的自主工作的唯一手段。」換言之,持續抱持終有一天可能成功的想像,強化並鞏固了此剝削結構,個人只有困在自己的失敗與挫折中,無力抵抗。
此種進取式價值與自我規訓深植於教育與文化中。舉例而言,國內與影視產業直接相關的院校科系包括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台藝大電影系、北藝大電影創作系、南藝大動畫所與音像所,畢業生多半是想當導演的年輕人。也因為電影創作、劇本寫作、甚至技術的難以教授,畢業生往往在對自己、對產業均認識不夠成熟的狀況下,奮力投入無間道般的試煉。全台灣包含技職體系的30餘個影視相關系所,一年數百位畢業生若投入影視產業,直接面臨的是破碎的勞動處境:一切靠天時地利人和、機緣造化看自己、不做做看怎麼知道自己適不適合,徬徨迷惑正是血淋淋的現實。高喊多年的人才培育(無論從演員到製片等每個環節)在缺乏穩定勞動條件與專業訓練的破碎環境中,自然難以積累,遑論加速成長。即使經過千錘百鍊、萬般磨礪,加之天時地利人和而浮上檯面的幸運者,成就了目前的製作產量,檯面下又有多少人浮沉於過勞無望之海,在其中勉力掙扎求生?
遲來的反抗,為時不晚
面對普遍低薪、過勞的狀態,幾個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到,有足夠休息時間是眼下最需要的,「人都需要休息,如果影視圈有週休二日,國片應該會變得很好看吧。」依依說。若要談提高薪資,則宛如無線迴圈地回到長期積弱不振的市場、無法回收的製作、已然改變的觀眾口味。或許抗爭與意識的萌芽早在1990年代向美國市場全面開放時就應該開始,儘管錯過最佳歷史時機,只要開始,何時都不算太晚。無論是《文化基本法》欲延攬進用文化專業人才,或者商業體系欲生產一個可回收成本的產品,只有先正視了業內工作者的真實處境,從下到上共同面對,才有可能位處於中美資本力量間拉扯的台灣,共謀一條生路。
(封面圖片取自網路,圖為馬丁史柯西斯在台拍攝《沉默》的劇照)
|
本文同步刊登於
《今藝術》雜誌2016年7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