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重要期刊《Inter-Asia 文化研究》刊出侯孝賢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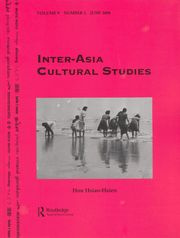
由交通大學陳光興教授所主編的亞洲重要文化學術期刊《Inter-Asia文化研究》(Inter-Asiao Cultural Studies)本期(第九冊第2期)刊載了由陳光興與英國電影學者Paul Willemen以及魏旳所合編的「侯孝賢專輯」。專輯內收錄了2005年陳光興在新加坡主辦的「亞洲侯孝賢:電影、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的多篇論文,包括侯孝賢導演的專題演講。由於Inter-Asia 為英文期刊,為使《放映週報》的讀者得以一窺專輯編者對於此一專輯在侯孝賢研究與電影研究所具有的意義,以及本期所收錄的各論文對侯孝賢電影所提出的觀點,週報特別為讀者節譯三位編者的專輯前言以及各論文的摘要。在前言中,編者一方面將侯孝賢電影放在從魯迅到陳映真以來的人文傳統中,來凸顯侯孝賢電影作者-知識份子的身份,另一方面嚴肅探討對一位電影人進行學術書寫的意義與可能陷入廣告誘惑與個人頌揚陷阱中。學術的文字或許讀來不甚容易,但是前言與各論文摘要對於侯孝賢導演的影迷以及對於電影有興趣的讀者,相信都會有新的啟發。
侯孝賢導演參加【打造一座電影城市】座談
專輯前言(陳光興、Paul Willemen、魏旳)
2005年四月,新加坡國際電影節製作侯孝賢電影回顧展以表彰他對於世界電影的卓越貢獻。配合這個回顧展,在四月29-30日兩天,由亞洲研究中心、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新加坡歷史博物館的贊助下,我們主辦了名為「侯孝賢:電影、歷史與文化」的國際研討會。
侯孝賢無疑是亞洲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幾位電影人之一。然而,要以何種批判的角度來檢視他的作品卻是一大難題。從與侯導一起籌備這個研討會的過程裡,還有在影展中觀看他的電影、聆聽他的講演,以及與他私下的閒聊或是正式的訪問裡,我們體認到,侯導的電影製作不能只從電影史的角度來討論。而是應該被視為是一個我們或可稱之為「中國批判知識傳統」的複雜產物與互動結果。因為侯孝賢的視界乃是由「中國」語言所架起的穹蒼所形塑,也受其所限。侯導與他同時代的其他電影人不同,他完全是在台灣養成,從未出國留學,也不諳外語。他的知識來源從來就是透過中文取得。事實上,他對於中文各種方言的使用非常講究,對語言的細微差異總是仔細處理。我們這樣說絕非是在暗示侯導是觀點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侯導的「中國性」是超越單一的國家主體之上。我們可以看到侯導不只提攜中國大陸的年輕電影工作者,他也不吝幫助馬來西亞與其他國家的電影人。在當代中國電影工作者中,侯導被公認為是對於支持新一代電影人最有心且不吝付出寶貴時間的一位。他經常幫他們搞定與各電影組織之間或是產業內部裡的一些安排,讓他們得以持續拍片。在本期整理成專訪刊出的對話裡,可以清楚看到電影產業對於侯導是一個策略場域。一個廣義的「大中華」電影圈在他的想像裡是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好萊塢電影無法輕易全面宰制的區域。
當別人問侯導他的知識養成受到哪些啟發,他最常提到的一位就是陳映真(1937-)。陳的年紀大侯導十歲,可以說是台灣二戰後的批判領域裡最重要的知識份子。他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他的文學創作,在創作於三十歲前的早期作品滋養了台灣一整代在威權體制嚴格控制下生活的知識份子。當時他的小說是年輕人了解本地生活狀態的管道,尤其是弱勢者生活的艱辛以及他們之間的休戚與共的緊密關係。他的讀者所感動的並非是傳統的社會寫實主義,而是這些作品讓他們深刻看見每日生活在殖民統治、內戰以及被迫現代化與遷徙的暴力中是什麼樣的一種精神狀態。失去家庭與摯愛,殺人與被殺的夢魘不斷在記憶中湧現,狂人的瘋狂世界,理想主義知識份子的絕望,這些都是他經常刻劃的主題。在他的作品之中有一種凝重不安的能量將讀者之間緊緊相連。陳映真自一九七0與八0年代以來,涵蓋台灣文學、音樂、小劇場與新電影等領域的文化運動作品便對於台灣有深遠的影響。侯導早期的電影帶有陳濃厚的人文精神。自八0年代初期起,陳的文學作品中即開始處理台灣左派歷史的禁忌議題,部份故事源自於他本人在六0年代八年的牢獄生活中與政治犯接觸的經驗。侯導在他的《悲情城市》之後的電影受到陳關注日據時代以來本土歷史影響很深。然而,由於陳映真長期反國民黨(因其右翼的極權主義)與共產黨(因其七0年代起的市場轉向),還有他鮮明的支持兩岸統一立場(與民進黨的獨立路線相左),因此影響力被刻意淡化與邊緣化。
不過,陳映真對於現代化處境裡的「小人物」生活既同情又批判的刻劃,並非是毫無所本。在不少場合裡,陳都指出魯迅(1981-1936)是他知識的啟發,甚或是他的故鄉。身處於清末民初,魯迅這位時代移轉時期的人物體現了傳統文人與現代知識生活樣貌的結合與延續…。儘管魯迅的作品在過去國民黨主政時期無法在台灣出版,陳映真的寫作正好補足了這個缺空,讓五四新文學運動得以在台灣延續下去。或者,我們可以說,是透過陳映真的作品知識思潮才得以保有一點與五四運動和中國左派傳統的連結。由於這些歷史關連與新關連,侯孝賢的電影不僅在台灣引起迴響,同時也在兩岸分離四十年後的八0年代起,在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圈被看重。
本期的論文集並非是要建立某種知識傳統的譜系來確立侯孝賢的地位。我們的目的毋寧是要展現更廣闊的知識空間,好讓侯孝賢的作品能夠在電影領域之外的空間得到應有的認識。不論如何,誠如魯迅與陳映真的文學或是其他寫作,侯孝賢的電影作品也是他表達思想與社會關懷的媒介。就像這些前輩們,他跨出自己專業領域的界限,積極發動或參與刻不容緩的社會改進運動。他最近直接介入政治的作為正是一例。他能夠呼召知識份子一起來反對政黨在選舉期間撩起族群衝突,反映了侯導不吝於與跨社會、階級、文化與國族的人士或異議份子一同努力。
《最好的時光》裡三段故事相互作用產生意義
書寫單一電影工作者的作品很難避免掉入一些陷阱裡。首先,愈來愈多的批評-分析論述變成行銷論述:在當前的媒體市場經濟以及學院裡,一篇論文(任何論文)都可能成為廣告的內容,廣告所促銷的產品不一定是論文所研究的作者或作品,當然有可能是該篇論文或該書的作者。現今這種陷阱要完全避免幾乎不可能,我們只能儘量減低對於研究論點本身帶來的傷害。第二種,也是更難自拔的陷阱是純粹想要去樹立一位藝術家獨特性的衝動。除了可能掉入廣告的牢籠外,這種論述完全與該作者為何在當下值得被書寫的理由相違背…。
這些關於侯孝賢的論文收錄在此不只是要凸顯侯導電影的獨特價值,也不只是要提出他的作品是如何「作用」的一種解釋。我們幾位編者希望這個專輯能夠提出一些關於電影意義傳達過程的問題,包括:如果我們完全不同的社會個體化形式(forms of socialized individuation)必須要化成電影的話,電影藝術家會認為電影應該做什麼以及被看到做了些什麼。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專輯某些論文所提出觀點的重要性可能超過作者本身的認知。令人驚訝的是,侯導的電影的特色同時也可以在世界當今其他地方的電影導演的作品中看到,這些導演都試圖傳達他們所掌握的在二十一世紀初特有既社會又個人(social-yet-individuated)的不同生存樣貌。這些特色包括:侯導被盛讚的連續鏡頭(sequence shots),他混合多種時間性的做法(不僅是過去與現在,還有自傳、主觀與歷史時間性),或是拒絕把他的故事侷限在單一的敘事框架裡,而是混合不同的劇情發展(例如,《紅氣球》的劇情裡包含關於這部影片製作的論述,或是在《最好的時光》裡讓三段故事相互作用產生意義)。除此之外,侯導與世界其他高度知性的導演一樣,毫不避諱地與介入電影圈這個完全工業化的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被機構化的各種面向:首先,他的電影無可避免地同時是深植於國家與國際機構的處境裡;其次,他也必須配合各電影製片所要求的國家與區域內部結構再製(reproduction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frastructures);再來,同樣顯著的還有他必須面對一個電影導演被視為「親密陌生人」(intimate stranger) 的多種狀況,因為電影(聯合)製作以及映演的條件必然會動員超過一般社會-文化組織的經濟與文化資源,但也受到更多的限制。
當然,侯導這些關注也見於其他影癡導演的作品裡,例如Bela Tarr、蔡明亮、賈樟柯、Chantal Akerman、Amos Gitai、Elia Suleiman、三池崇史或是Alexander Kluge等。不過,任何試圖了解侯孝賢電影如何提出與闡明這些議題的嘗試不會僅是對他的電影作品的解釋,而必然也是對電影最終極層面的探討,也就是,電影在今日如何負責任地「有/製造意義」(make sense)。
本專輯感謝所有研討會的與會者。雖然研討會籌備的時間倉促,但是所有受邀者都熱情回應。這也反映了侯孝賢三個字所具有的獨特魅力。我們幾位編者特別感謝蓮實重彥教授所提供的專題演講論文。本專輯謹獻給六十大壽的侯孝賢導演。(林文淇譯;侯孝賢座談會圖片取自「台灣電影網」)
專輯論文摘要
電影與歷史:批判性的反思(侯孝賢;劉奕德英譯)
侯孝賢受邀至新加坡談論他自己。在座談中,他把焦點放在他的家庭背景、童年回憶、生活經驗和這些經驗如何影響他的生命,以及他如何製作他的電影。此外,台灣經歷過了許多政治和經濟上的劇烈變革,尤其在解嚴之後,這些因素影響了侯孝賢的人生,也影響了他的電影。換言之,侯孝賢的電影不只展現了急速都市化下鄉村社會的改變,也呈現了台灣歷史中的重要事件。在談話的結尾,侯孝賢也提到了瞭解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之後,他想要更投入公共領域之中為社會做一些貢獻。(洪健倫譯)
雄辯的靜默:一篇談侯孝賢的散文(蓮實重彥)
在蓊綠小山城所拍攝的彩色片《戀戀風塵》之中,有兩段近似於盧米埃在十九世紀末所拍攝的黑白無聲短片《火車進站》和《穿過火車隧道》。侯孝賢場面調度之中的靜止不動攝影機〈fixed camera angel〉以及長鏡頭〈long take〉,反而成為他所有電影作品的動力機制〈means of transportation〉,調動了戲劇元素、把運動和動態〈motion〉引入了銀幕畫框之中。
在他早期的三部愛情喜劇〈三廳電影〉中,豪華轎車象徵了新富階級,而機車則象徵了一般大眾或窮人;開轎車的都是年輕女性,然而汽車空間顯然是不太適合談戀愛的地方。在《尼羅河女兒》和《南國再見,南國》之中,想要逃離的男人,卻無法經由汽車來達成逃亡和得到保護。
相較於這些片子裡汽車的負面涵義,從不同角度所拍攝的行進中的火車,卻提供了更加豐富和深厚的涵義。當攝影機擺在火車車廂內,就像《戀戀風塵》中的阿雲和阿遠搭火車上下學,即使二人靜默不語,但彼此的親密情感卻不言可喻。但如果攝影機是擺放在鐵軌旁或月台上,情況就不同了。《童年往事》中,祖母攜著孫子要「走路回大陸」,在路邊小店喝冷飲休息時,恰好一旁開過了一列載貨火車,象徵性地強調出祖母對於大陸的孤獨鄉愁。《悲情城市》中,聾啞攝影師文清,攜家帶眷站在月台上茫然地躊躇逃亡那一幕,火車在他們面前疾駛而過,是侯孝賢對於他們那種無力感的崇高描繪。到了《珈琲時光》,洋子和肇也是坐在電車車廂之內,二人同樣靜默無言,情感卻也同樣親密默契─在如此靜默的時刻和場景〈taciturnity〉,呈現了一種毋需慾望語言〈sexual language〉的愛情。(陳平浩譯)
《戲夢人生》是侯殖民歷史書寫的例子
台灣與南韓的後殖民電影歷史書寫:《戲夢人生》與《醉畫仙》(Kim Soyoung)
這篇論文所要討論的是:後殖民歷史書寫〈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銘刻在電影之中的方式。本文將比較的兩個例子,是侯孝賢的《戲夢人生》以及南韓導演林權澤〈Im Kwontaek〉的《醉畫仙》,不只去探究這兩部片中的去殖民〈解殖〉電影運作〈de-colonization in cinematic apparatus〉,也試圖去理解片中所承載的殖民歷史。後殖民電影的概念,作為一種歷史檔案的另類建構法〈altern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ive〉,試圖把電影實踐放入記憶貯存、歷史書寫、電影再現、社會記憶…等等所交織而成的複雜場域之中。這兩部電影可以當成這種後殖民歷史書寫的例子:在此時全球化的觀影環境之中,它們提供了一種後殖民認識論〈postcolonial episteme〉,藉以回顧斷片一般碎裂的過去,再現了幾乎不可見的歷史檔案,以及提供了一種由影像所預示出來的未來。(陳平浩譯)
侯孝賢:評價台灣新電影的標準(聞天祥)
將侯孝賢電影置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與美學,本文透過其電影與台灣電影史發展的緊密關係探究侯孝賢創作取向轉變,以類型與作者論、片廠制度、流派影響、台灣法規、片管制度、電影節、電影獎項、票房、與影評等切入點分析電影,並按照時間順序,從較早期的電影與其經驗來檢視侯孝賢常被忽略的早期取向,接著以釐清侯孝賢於台灣新電影的角色與整體關係。 本文討論侯孝賢如何成功地匯集新電影不同的力量,創造出導演們能夠相互投入對方製作的模式。 這些社會文化上自覺的電影,包括了侯孝賢的《兒子的大玩偶》,均富有藝術感,並且從戒嚴晚期新興的中產階級迅速得到支持。透過討論《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本文描繪了新電影的票房挫敗以及導致於1984年宣言發表的媒體對峙。論及台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之重要性時,影響台灣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深遠的《悲情城市》會被特別強調。 本文最後聚焦於《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與《千禧曼波》,不同於以往,侯孝賢展現了在敘事中形塑時空的興趣,在這一連串的討論中,侯孝賢與台灣社會環境的互動重置於他從商業電影導演轉變為導演作者的回顧路徑,從對社會的關注到對於政治的涉入,侯孝賢作品通常被視為台灣電影發展史的里程碑。(林譽如譯)
《海上花》是個微醺之夢
侯孝賢的電影:追索歷史、逃離歷史(戴錦華)
這篇文章把侯孝賢的電影放在一個後冷戰全球化的場景(post Cold-War global setting)之中來分析。侯孝賢電影研究最常見的二種詮釋取徑,法國的「作者論」(auteurism),以及「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本文將把這兩種取徑研究取向,放在冷戰情境以及後冷戰全球化的政治脈絡之中,來加以考察。
侯孝賢和中國第五代導演,幾乎同時在國際影壇上崛起,但卻呈現出一種平行對比的關係:侯孝賢愈來愈政治(political)的台灣三部曲,但中國第五代卻相反的「去政治」(apolitical)。然而,這種相反的趨勢,其實有相似性:二者都是在各自獨特的社會脈絡中生產另類政治(alternative politics),二者也都各自在重新建構新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本文將聚焦討論侯孝賢的台灣三部曲、《海上花》、以及《珈琲時光》。(陳平浩譯)
侯孝賢的兩則光影之夢(黃愛玲;王慶鏘英譯)
傳統中華文化中,夢通常不只是一種敘述的手法或是作者想像的延伸,而是冥思生命的工具。本文試圖從夢的觀點研究侯孝賢在《戲夢人生》與《海上花》的美學。前者像是一場神智清晰的夢,夢中之人就是年老的布袋戲大師,而製片者侯孝賢則是閒逛進夢裡並將之記錄下來的過客。而後者,相反的,是個微醺的夢,一個個段落鏡頭(plan-sequences)在此藉由淡進與淡出(black-ins and black-outs)被編織在一起,成了一場像是沒人想從中醒來的夢。
《好男好女》開始著眼年輕一代與他們的城市文化
發生了什麼?侯孝賢的故事、場景與音效(Adrian Martin)
每次第一遍看侯孝賢的電影時,反覆遇到相同問題是:在整體故事線與單一場景中,發生了什麼?這是侯孝賢獨特電影風格所帶來的困惑,細緻、自成一格、且又豐富,同時也交錯衍生了電影文化政治上的複雜意義。 透過處理這樣唯美的困惑,我們可在兩種主要討論侯孝賢電影的態度間找到出路:一是局內者閱讀,主張電影對在地台灣歷史錯綜複雜的指涉;二是局外人閱讀,把電影簡約在特定的時空,並且宣揚其形而上的抽象無限性。 事實上,侯孝賢電影為所有具有政治訴求的電影提問並找到一個答案:一部電影如何與歷史嵌合、同時又分析歷史? 在一定的敘事安排上,完整使用「背景故事」(一個故事事先透漏什麼在銀幕上被講述的部分)和較易辨識的遮蔽作用,這種嵌合方能達成。 更細緻的場景與鏡頭加入的下一策略,即特別屬於侯孝賢的一種擁擠的場景調度和音效設計的使用(直接收錄的聲音氛圍與配樂重疊的混合),於當代亞洲電影脈絡裡是相當創新的。 本文專注於侯孝賢量產的時代,從《好男好女》(1995)到《珈琲時光》(2004),也就是他靈感再起、開始著眼於年輕一代與他們的城市次文化,本文同時詳盡地檢視《好男好女》中一場景之壓制觀念來總結。(林譽如譯)
侯孝賢如何改變台灣電影?一個批判性的重新評價(魏旳)
自從1980年代起,侯孝賢便是台灣新電影運動當中的重要份子,更在之後逐漸崛起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電影大師。然而,就在同一個時間點,台灣電影產業戲劇性地縮減,甚至接近整個崩潰瓦解的程度。根據布爾迪厄的文化再製理論(cultural production)及其中關於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本文將侯孝賢視為一個社會行動力(social agent),以進一步分析他與台灣電影產業轉變的結構因素之間的動態互動關係。侯孝賢似乎從一開始便是主觀地選擇拍攝與製作電影的方法,但事實上他在當時所擁有的可能性是被社會結構所限制的。此外,他的成名軌跡也深崁於全球文化經濟的動態歷程。弔詭的是,伴隨著同樣的在地與全球歷程,台灣電影產業卻嚴重地衰退。(林蕙君譯)
侯孝賢的歐洲影評(Valentina Vitali)
在電影院還很難看到侯孝賢電影的時候,歐洲的平面媒體上就已經出現了有關侯孝賢電影的評論。本文要問的是:在此背景下,這些影評的功能是什麼。透過檢視具有代表性的影評,我認為這些影評並非只是在妥協製作、發行以及映演之間的關係,而是細微緩進地灌輸歐洲大眾新的觀看電影的方式。在歐洲電影院終究屈服在好萊塢製作公司愈來愈具侵略性的行銷策略之際,儘管數量稀少,具有作者標記的侯孝賢電影便成了在歐洲販賣好萊塢電影所必須的「教育性」再編制(educational realignment)。(林蕙君譯)
相關網站:
Routledge 出版社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網頁: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journal.asp?issn=1464-9373&subcategory=SS280000 (對於刊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線上訂閱期刊)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官網: http://www.inter-asia.org/journal/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