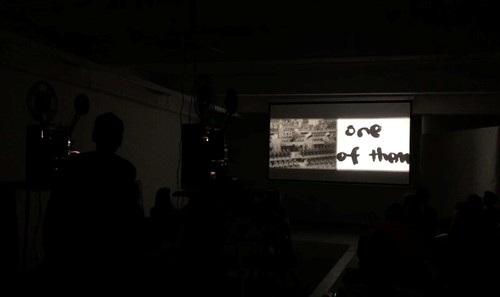【2022 TIDF】公轉自轉,讓攝影機繼續轉──手作的光影與情感:訪實驗電影創作者徐璐

台灣實驗電影創作者/藝術家徐璐,近日剛畢業於加州藝術大學(CalArts)影像創作碩班,在美國多年學習影像創作並持續從事創作實踐,創作主要以膠卷為媒材,也製作影像裝置和進行現場/擴延電影演出等,作品曾入選鹿特丹、多倫多、紐約電影節等國際影展和藝術展節。本次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特別邀請她的三部作品:2018 年使用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完成的《短短的歷史》收錄在探索檔案影像再製作品的「記錄X記憶:檔案變形記」單元中;2019 年創作的《臨摹(另一種版本)》收在「台灣切片|真實的呢喃:1990s 以降的女性私電影」單元中,作為臺灣女性影像創作史脈絡中的一個標記;2021 年完成的《公轉休眠(還在自轉)》則放在回應疫年狀態的單元「比紀錄片還陌生:潛未來」中。
可以說,不管是在過去或未來的時空中,徐璐都以影像創作持續不斷地紀錄並反思身處的當下,也回應她所關注的主題。本期《放映週報》特別訪問徐璐,請她聊聊她的實驗電影創作啟蒙與歷程,分享本次展出三部作品的背景,並暢聊她對於實驗電影的見解和觀察。
——請向《放映週報》的讀者介紹一下自己。你是什麼樣的創作者?對於創作媒材的選擇有什麼喜好或考量?為什麼選擇以膠卷創作?
徐璐(以下簡稱徐):我的作品多為實驗短片,也會做裝置,和擴延電影(Expanded Cinema)的表演。在美國讀書時接觸到使用膠卷的技巧,作品多使用電影膠卷。我對觸感視覺、抽象音像、情感記憶很有興趣。主題圍繞在日常生活物件中,以攝影機去「表演」某種凝視,寄之以情地去處理原生家庭、身份認同、私人情緒等等在心裡的結。
我從小似乎就是一個對情緒很執著的人,會很衝動地想解決掉不舒服的感覺。這樣的執著跟衝動,在我的影像創作裡變成一個「思考著的行動」。它來自一種很寂寞、很孤獨的狀態,所以很需要能自己一個人,用手作、很直覺的方式,去補捉能昇華那些情感的光的質地。因此,我仍然偏好依賴膠卷轉譯光的細緻度,讓我能在一個人創作的狀況下,還是能達到特定的質感。另外,膠卷創作本身可以有很多變數(如何曝光、轉印、沖洗、刮、畫、投影的方式等等),在越來越熟悉其特性後,可以玩的東西也越來越多。我對挑戰各種技巧很有興趣,也就越來越投入其中。
——你認為實驗電影是什麼?就你自己創作和個人經驗來說,如何定義實驗電影?
徐:我的理解比較是:電影一開始就是充滿實驗的。電影剛發明時,藝術家幾乎都在探索這樣的動態影像可以對觀眾產生什麼不同的觀感。法國導演/學者潔嫚・杜拉克(Germaine Dulac)在 1920 年代發表的文章〈From Visual to Anti-visual film〉中稱電影為「第七藝術」,說明電影之於其他藝術有自己無可取代的性質。而這一個特質,是建立在電影的視覺怎麼讓觀眾去感受那些肉眼無法直接感受到的感官、情緒、節奏、律動、時間性等等。杜拉克在文中提及:「電影當然可以去說故事,但你要記得故事什麼都不是。故事只是一個表面。」電影不需要去屈服於劇場或文學,不需要被強加隱喻,因為它本身就蘊含純粹的視覺感受。杜拉克也說,電影在其他藝術中,它被感受的方式最類似音樂。
而到了當代,仰賴於敘事的音像作品依然為主流。我會說有一派的實驗電影創作者或多或少還在繼續探討電影的本質,但在這個「探討」裡,與其注重「研發」,他們更注重個人內觀,以及對「純粹電影」(Cinéma Pur)的修行,我個人的作品比較依賴在這個脈絡。
我其實希望實驗電影可以是一個不斷變動、海納百川的形式,各種挑戰觀看慣性的作品,都可以稱上實驗。只是我一直在思考,這個類型名稱是不是已經只是一個包袱了。經過一百多年之後,被稱為「實驗電影」類型的作品,也有了某種模式或慣性,在提供創作者一個停靠港的同時,也成了某種一個緊箍咒,他們似乎就必須提供新穎、「進步」的實驗(我偷偷稱有如此想法的創作者為「達爾文派」)。其實撇開影展和競賽場合,實驗可以是很個人的,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節奏跟自己要處理的事、處理的方法(又很無害)。我甚至覺得,有手法或內容雷同也很好,那也是一種文化歷史的共同紀錄。
——你在加州藝術學院(CalArts)的求學經歷,對你的創作有沒有什麼影響或啟發?
徐:其實來 CalArts 之前,我在紐約的經歷更大大地影響了我的作品跟認同的社群。首先,我在新學院(The New School)老師喬爾.斯來莫維茲(Joel Schlemowitz)的「回收影像及 16 毫米無攝影機電影」課堂上,從實驗電影創作者海倫希爾 (Helen Hill)的集合著作〈Recipes for Disaster〉開始爬梳實驗電影脈絡,了解手作膠卷這個遊走在業餘、獨立、叛逆之藝術創作方式以及它催生的社群。
我們在透明膠片、黑色膠片、拾得影像上刮畫跟剪接,我一直是個喜歡手作、手繪的人,創作過程中可以直接看見畫面、手工處理那些影像,讓我很直覺地繼續去使用這個媒材。我在這堂課做了《短短的歷史》,當時,受老師邀請來課堂上分享的一位創作者,也出席我們的期末放映。放映結束後,她衝來跟我說,「你以後一定會做出很棒很棒的作品。」這樣直接的反饋深深地鼓勵我,原來做一個這樣隱晦的作品,是有人懂的,也從此愛上了這樣純粹慶祝型的放映會,那是一種很感人的場合,創作者彼此肯定一路來的成長。
紐約緊密的藝術家社群,跟遍地開花的放映會深深地影響著我。我覺得,自己想做的作品很被保護在這樣重視個人電影、業餘電影、抽象電影、單純就是在玩技巧的電影、投影表演、或結構電影等等的環境之中。我的老師 Joel 要求我們每學期參與幾次實驗電影放映。在紐約有一群實驗電影創作者、藝術家緊密地與實驗機構和場域共生,包括電影資料館 Anthology Film Archive、藝廊 Microscope Gallery、影像後製電影暗房 Negativeland Motion Picture Film Lab、電影藝術非營利組織 Mono No Aware等地方出沒。美國日記電影代表創作者約拿斯梅卡斯(Jonas Mekas),我也常看到他生前在 Anthology、Microscope 等據點出沒。
我第一次校外放映《短短的歷史》就在 Negativeland 亮相,開啟日後諸多展映交流機會。除了 The New School,我當時也在 Mono No Aware 上了許多工作坊的課,接著擔任志工、成為助教,然後變成講師。除了創作技巧日漸成熟,也得到許多辦工作坊、放映、影展活動的經驗。當時是在這個環境之下,即使社交焦慮也要把自己拋出去認識人、去學習、去做事。然後看著前輩們的作品,看著這些自主經營的社群,也成為他們的一分子,也深深受他們的影響,也開始思考要怎麼經營自己的社群。
考上 CalArts 之後,搬到洛杉磯,社群環境很不一樣,但學校基本上讓我非常自由。CalArts 有幾位教授,像是 Betzy Bromberg、Charlotte Pryce,她們本身就在做抽象的 16 毫米作品,所以,老師通常蠻能看懂我想做什麼,或是不懂的時候,也給我空間讓我去掙扎。影響我蠻多的是課堂上批判作品的方式:老師同學間有一個默契是會先感覺、嘗試理解同學的作品,當然還是會有個人喜好,但是,在一群敏感的人之中,能聽聽別人第一手感受到什麼是很幸福的,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去度量自己的作品。換句話說,我到了一個更保護我作品的環境。總之,我在學校裡面似乎如魚得水(註)。
—— 在你個人網站的作品分類中,《短短的歷史》被歸類在擴延電影(Expanded Cinema)中而不在電影作品(Film)中,請問這件作品原本規劃就是以現場放映演出為主嗎?這件作品是怎麼產生的?創作發想過程如何?
徐:啊,被你發現了。我是很近期在整理網站的時候,才把《短短的歷史》放在擴延電影的範疇。通常在講擴延電影,最直覺地會想到的是在現場的投影播放之外,可能還會搭配現場的聲響藝術、操弄投影、多重投影的現場表演等等。我會把這部作品放進擴延電影是因為最近一場放映會,我使用兩台 16 毫米投影機放映,我會試情況,快速關閉再開啟其中一台投影機,好讓兩台放映影像更同步。一個朋友說,這也是一種現場表演,我後來想想,就把這部片放進擴延電影。
這部片是在課程上完成的,最初就設定要用兩台投影機播放。那時後教室裡有一整個鐵櫃,擺滿了 16 毫米的老舊膠卷讓我們隨便使用,裡面有像是職場安全、文史紀錄片、科普影片等美國教育影片。我很直覺地拿起了其中兩卷膠卷「中國共產主義」(Communism in China)和「日本奇蹟」(Miracle in Japan),才意識到跟台灣都很有關係。我以第一人稱虛構了一個無名又無辜角色的回憶錄,其實是以台灣歷史撰寫的自白,講述台灣從本來是中國領土,後來被日本殖民,到被中華民國登陸的政權流變。創作期間,剛好許多台灣藝人(被迫)錄製影片或發聲明稿說自己是中國人,以及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國政府囚禁,在這樣緊張憤怒的氛圍中,我當初創作寫下的第一句,其實是最終作品的最後一句話:My name is Taiwan(我的名字是台灣)。
—— 《臨摹(另一種版本)》令我想起「情感物件」的概念,以及跨世代記憶互相輝映、傳承,甚至回饋的可能,請問當初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作品?
我時常從手邊可得的器材來想作品。當時在 Mono No Aware 工作,因為一場 35 毫米的工作坊,而有了借用 35 毫米器材的機會,Mono No Aware 除了提議我做作品(註),還給我400 英尺的彩色負片,完成後與工作坊的作品和一起沖印。我當然欣然接受。
那陣子,我因為伴侶暑假回家鄉,有強烈分離的焦慮,也一直很想處理在情感關係裡的各種憂慮和焦慮,就想起原生家庭父母的關係。於是乎,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伴侶留下的光轉印紙(Sunprint Paper)出發,我開始發想作品。滿天星和父親寫給母親的情書,這兩個物件是我從小對雙親情感的印象,於是就想到拍攝這兩個物件藍曬的過程,或留下的影子形狀,就好比父母關係或許影響著我的親密關係。我其實也搞不清楚我真正的感覺,所以,與其說是有目的地去捕捉什麼,其實這部作品比較是一個冥想,用鏡頭去吸氣吐氣,分心時讓感性席捲一下,再把注意力帶回來。冥想過後像是得到一個和解。當初是這樣想的。
—— 《公轉休眠(還在自轉)》像是《臨摹》藍曬光影試驗的延伸,只是臨摹的是你自身的生活/勞動狀態。請問,這件作品是原本就想好才創作,或是比較隨筆的狀態呢?
這部作品比較像是我想把自己拎起來工作而做的,也的確是一部疫情狀態下產生的作品,可能可以把它看成每日的自主訓練。原本只是想說,這些灑進我廚房的光好美,想拍下來。但畢竟用膠卷捕捉還是會多想一下。
我一開始學習拍攝 16 毫米和 8 毫米時,深受「一捲電影」(Camera Roll)拍攝手法的影響:意指剪接是在攝影機裡完成的,第一個鏡頭就是第一個拍攝的,依此類推,拍攝時已經把作品的節奏、長度、鏡頭順序考慮進去。雖然這部作品還是有進數位剪輯過,不過大致是依照拍攝的順序。這部作品也可以看成一個月曆/月記電影(花了約一個月完成)。拍攝過程和自己約定好,即便再不想做事,每天就拍一個鏡頭,當作給自己的一個交代。我其實已經估算好光會經過的時間,把攝影機構圖調整好,設定好間隔攝影,就放在那邊,之後再來收成。然而,我很快就發現,拍攝過程中根本不能休息;攝影機的存在感很強烈,被觀看的感覺很強烈,我因為生活在場景裡面,有時候就是得走進裡面做事,後來乾脆開始玩起人造光影,也因此作品中間才會有一些比較表演式的鏡頭。
——本次沒有放映的《阿嬤的剪刀》(2021),也可以看見你的創作脈絡:世代與記憶傳承,以及對於自身根源的探索,這樣的創作主題還是現階段會繼續延伸探討的嗎?或是你近期有其他興趣?
對,我對世代和記憶/技藝傳承一直都還蠻有興趣,也會繼續做這樣的主題。在《阿》片中,我回憶阿嬤常常很得意地跟我說她年輕時做裁縫的故事。我嘗試讓攝影的運鏡、觸感還有裡面昇華的情感記憶變成像有溫度的織布一樣,從這裡去結合我與阿嬤的技藝,述說可能我的手巧或敏感度遺傳自阿嬤。
歷史造成的代際創傷(cross-generational trauma)也是我一直以來很想探索的主題。這樣類似的創作邏輯也會在我最近在做的作品《撿起放下墜落提起》(it follows it passes on)(製作中)裡面看到。是一部關於我對金門的記憶的作品,也算是在處理我跟父親的關係的作品。其實一開始是看了《斯卡羅》(2021),裡面提到的「撿船」讓我想到跟爸爸在金門一起長大的朋友。這位叔叔是一位文史工作者,小時候去金門就會到他家玩,看他從海邊撿拾回來的破瓷器,他會告訴你這可能是哪個朝代飄上岸的。
我從這個點出發,把從台灣帶來美國,但卻被我打破的杯碗帶到海邊拍攝,去想像過去金門海邊曾經的狀態,以及老一輩對於海邊因為長期戰事而造成的創傷記憶。我也一直記得他告訴過我:「我們在防空洞躲砲彈的時候,只能拿香來照明。」我想像這個意象,用底片拍攝長時間曝光的香,再用光學印片機複製單格畫面,拍出明明只有單隻香卻燒得明亮的動態畫面。後來我把這小部分的影像製作成一個 16 毫米的迴片(loop),用投影機播放,做成一個裝置作品《香火》(until there is no more sound from afar),去想像父親在經歷八二三炮戰後「一三五打、二四六不打」的童年、青年時期。
其實一些長輩知道我有在創作後,都會不約而同地跟我說,金門的影像一直都還是軍事影像,希望有比較文藝的觀點。前幾天我才突然意識到,啊,也許我有記得這個,我可能有做到他們所期望的(只是我也知道目前作品可能還是偏向隱諱、偏難理解啦。)。關於自身根源的探索這部分嘛,我會說我其實還是很不知道怎麼解釋自己,所以也可以說我這個脈絡的作品算是做來認識自己的。
—— 你也是台灣發起的實驗電影團體「ReaRflex 後照鏡」一員,是不是也受到在美國實驗電影社群的觀察和參與經驗影響?
「ReaRflex 後照鏡」的組成與其說有什麼偉大理念,不如說是一個自然而然,甚至是一場玩笑式、搭順風車的方式組成。我很崇尚自發性的活動,成員們有點衝,有機會打游擊辦放映就一起衝、就組了一個團體,其中最大的優點是不需要用自己的名字發聲,可以躲在團體後面認識新朋友,對不喜歡聚光燈的人很好。我真的受不了太多注目,雖然,最近開始發現有時候被注目會有點好處,可以幫助想做的事被看見⋯⋯。
目前只要一場放映有賣出大概三十張票,我就很滿足了。依這樣的脈絡,實驗電影創作者會需要小圈圈互相扶持,主要還是因為能掌握呈現自己作品的主導權吧?做作品的方式已經夠獨立了,大家都辛苦,能共享資源,互相幫忙還是更好。更重要的是也是很能理解彼此做作品的方法,所以能有實體的(拍攝、活動等等)支援,也有精神支援(對於作品的關愛)。
—— 接下來有什麼新的計畫呢?
研究所畢業後,就先繼續待在洛杉磯工作,希望能在業界做一些電影後製方面的工作,同時遠端地跟在台灣的創作者朋友辦自主放映之類的活動(再請大家多多捧場!)。在洛杉磯這裡可能會有一些兼差教職的機會,但希望能同時去一些地方做駐村藝術家,教工作坊,也還會繼續辦放映。主要還是先穩定收入來源,但期許自己還是用力的「玩」。
疫情穩定之後,希望能定期回台灣跟朋友一起辦實體的工作坊、放映會等等,慢慢累積社群,然後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在台灣做一個藝術家自主沖印實驗室(Artist-Run Lab)。■
.封面照片:《公轉休眠(還在自轉)》劇照,徐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