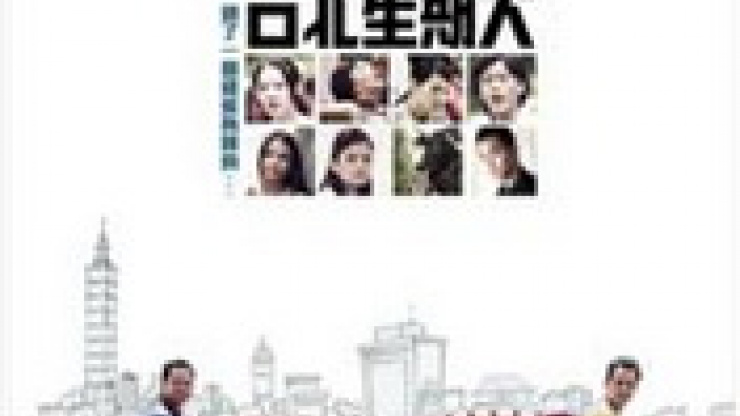《青春弒戀》:倒楣德昌瘋狂A片

論及《青春弒戀》,似乎容易無盡地陷入泥水仗,辯稱這創意來自《海鷗》、那點子出自台灣新電影,藉此擡高電影價值,但對這些戲法的實效,我說「諧仿」(parody)一詞足矣。諧仿以冒犯取樂,本質上不大禮貌,但除了煞有其事的英文片名,該如何解釋《青春弒戀》同時冒犯了契訶夫(Anton Chekhov)和新電影?
致敬或冒犯?
從互文層次看火車站台和解結局
有兩組被賦予強烈美學動機的物件首先值得一說,一是電話/手寫信,二是舊式交通站/新型大眾交通。姚愛寗飾演的 Coser 綺綺用智慧型手機在空屋亂打兩輪假情色電話(概念明顯混自楊德昌的《恐怖份子》〔1986〕和《麻將》〔1996〕),而第二輪情色電話於故事的次序與音畫處理又更關鍵。此處的安排是,主角郭明亮於台北車站伏擊玉芳與小張不果,潛回空屋,偶然撞見綺綺跟友人擅闖戲耍。綺綺打起情色電話,講到一半便旁跳(cutaway)出全片甚少出現的台北夜景空鏡頭,綺綺的聲音此刻也被後製上類深夜廣播節目的回聲效果。不難指認出,明亮的大庭廣眾兇殺與綺綺的漫市浪語淫聲,此刻雖無因果交集卻有形象疊合,無非要人相信這組「新浪」代表的行動與語言,各自將台北表徵為一個沒有溫馨的暴力地方。
舊式交通站如船港、火車站台主要出現在片頭與片尾,而其作為小張的介紹(intro)與結幕(closing),也不是巧合;這選景的重要邏輯是,火車與手寫信為同脈的情調構成元素,玉芳與小張稱之老派,恰好與「襲擊」(故事或象徵上皆然)二人身心的都會浪潮對立。下鄉勞動兼療傷的懷舊印象還不約而同地還魂於稍早的《瀑布》(2021)、《消失的情人節》(2020)等台灣電影——在此暫且不論旅遊廣告式的印象(鄉村與勞務階級成為都會人掠取心靈安慰劑的腹地)可能更貼近某種過時的城鄉想像——若新浪與老派的對立甚至能拓展至人物際遇的對峙,亦即,明亮與綺綺的青春早夭/無緣,對峙於另一廂玉芳與小張的心智成長/重逢,那手寫信於片末再度出現時,據此一路將結局推向玉芳與小張在宜蘭鄉間火車站再會,可謂理之當然。

這「理之當然」只是情節邏輯上的。推進到互文建構的層次,要面對的一大疑難是,假設前述新浪/老派對立建立起的情調有效,會不會叫新電影與契訶夫的支持者不得不懷疑電影後半的一句台詞「你只相信新聞,不相信我嗎?」是自我調侃:「原來這部電影止於贗品層次,所以沒什麼好相信的?」就互文建構,新浪/老派兩組男女際遇之對峙便是稱《青春弒戀》為諧仿的最好例證,原因在火車站台和解的結局對新電影與契訶夫不禮貌到極點。
這場戲無禮,因為新電影與契訶夫晚期戲劇的基礎至此無影無蹤:看倌們可以反事實地想,如若櫻桃樹砍倒還能接回、海鷗打死尚可復甦、現代性火車當真能駛回前現代、楊德昌的台北人還能透過出走台北來自癒,不就像是在說舊世界的維度原來如斯淺薄,是從居住地走去交通站即可梭入的曩日,怎可能使人犯上身陷譫妄之境的風險硬舉往事牛刀亂揮?新電影或契訶夫的創作(尤其是《海鷗》與《櫻桃園》)都立基於舊社會物質基礎消逝,而《青春弒煉》火車站此處「再續前緣」,毋寧是透過快捷的撫慰效果,暗渡陳倉著往事並非往事、過去從未消亡。
《青春弒戀》「就是」諧仿春宮
精緻情色視覺策略內的拙劣片中A片
無論如何拼接創意,「鄉間火車站再續情緣」終究反向狠揍了新電影和契訶夫一拳,但《青春弒戀》歪成一部褻瀆典論的諧仿戲是否重罪難赦,我不大關心,更在意若要進一步往下舉證《青春弒戀》的贗品感,是否能以迷影心態娛虐地說,「意淫」一詞在此不是類比式的,因為《青春弒戀》不光「很像」色情片,而是「就是」以新電影與契訶夫劇作《海鷗》為基礎的軟調色情諧仿春宮(porn parody)?
先從調度與攝影機運動切割出的生活空間下手,電影中生活空間的質地真的近似都會夜店或情色旅館。幾組頗具宣傳效用的鏡頭,甚至花費大把精力拍郭明亮夜半窺視卧墊上的熟睡女體,並在置入銳器、愛撫的圖像聯想之餘,將整個視覺空間豔抹到仿若廉價遊女的肉身。將春色男女類比為世界成對的異界妖魔、異性只能以相互侵入(插入)的行動定位彼此,諸如此類的視覺策略,其實是在邀約觀眾同攝影機來一場視姦,滑稽地勾起我對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彩色片,甚至義大利鉛黃電影(giallo)的視覺記憶。
更細緻地說,從《幸福城市》(2018)到《青春弒戀》,何蔚庭進一步推展他對中景平面空間(flat space)的怪誕迷戀。那些關鍵的定場鏡頭或情感刺點突出的金錢鏡頭(money shots),畫面通常沒斜角,只有正面平視或垂直俯瞰,運動不搖不擡,限制框中人與物於不移動、垂直走、縱向跑。物件的直面描繪(frontality)在平面空間被強化,透視感則消失或侷限於單點透視。這自然不是人眼習慣的視覺,而是捲軸、掛畫,甚至網路頁面的世界。就調色與光影主題,《青春弒戀》肆意仿效俗艷的粉色、肉色、絳色、白色霓虹燈(neon light),幾近濫用。這不限於夜戲,因為鏡頭下的白日台北多覆著一層懨懨無生氣的鉛灰色好烘托特定的色彩主題,像那身白淨淨的學生服,在綺綺對郭明亮故作忸怩地示好時散發異質的情色感。粉色帘、肉色沙發、白色學生服皆成慾望高漲的視覺印記,不斷召喚觀眾將人物間的相處模式情色化,最後以綺綺騷撓夜城的「假」情色電話作結。

暫且不細分情色與色情(erotica and pornography),一個奇妙的戲院狀態是,《青春弒戀》順應觀者淫願設置視聽餌料,誘人奢靡浮華地凝視男女春色,將台北與慾望濾鏡下的台北不加劃分地擺在一塊,卻又將 Monica 以 Missy 為化名拍攝並引起郭明亮強烈慾望的成人網美直播影片,布置得像是一支對真人色情影像的拙劣仿冒品。於是,觀眾在戲院看著一個電影工業的產物,運用著具電影感的戲法,講述兩個人物對著連戲劇世界外真實素人自拍都不如的色情片手淫。若不將這當成寫實技法的失誤(那麼假的 A 片還能讓人有性慾?),這狀態幽默地具有後設性質,像是將拙劣的色情影像利用來製造具電影感的色情,而且帶點「誰比誰更色」的較勁意味,彷彿觀眾會因為從後者產生更大的快感而更認同《青春弒戀》。
何以變為性愛殺伐(沙發)旅(safari)?
《台北星期天》到《青春弒戀》的平面空間分析
叫人哭笑不得的也是,何蔚庭犯了作者癮佈下的反身性,更透過印象類比,加倍將前述的空間與色彩主題推往軟情色片的詮釋方向。《青春弒戀》不大呈現真正的網美色情片長什麼樣,卻對意淫居住空間別有一番用心,用心到何蔚庭以身作則地以成名作《台北星期天》(2009)當反例——蕭姐那間情色按摩室,後景的電視竟播著《台北星期天》。姑且不管此一安排的寫實性問題,這個「自我致意」以其兩面性提供叫我費解的自毀式互文:《台北星期天》旨在符應兩個菲律賓人滿市漂流的全局迷失感,才會不論何時何處、水上陸上皆做出以紅色沙發為核心的平面空間(強調直面描繪的「全家福照」),《青春弒戀》中蕭姐按摩室的功能、陳設著的肉色沙發,卻明擺著叫這「台北何處皆我家」的主題成為「台北何處皆炮房」的襯底(後景家具)。
俗艷的調色、沒有深度的平面空間中,幾個青年人物玩遊戲、想要成名、想要交男女朋友的空虛偶爾會被串回原生家庭失常與伴侶關係失能,然而《青春弒戀》最耀目的是始終平板「活」色——生活平面的荼靡春夢、被情色籠著的生活連環畫。
曾經的紅沙發日午曳航,何以變為肉色的性愛殺伐(沙發)旅(safari),而影像甚至主動提點觀眾這困惑?回望當初何蔚庭以新進導演之姿輕巧顛倒北市住民與外勞之敘事主客,更叫我深感荒誕於 11 年後的《青春弒戀》會一個勁地將台北青年、阿宅、尼特們說成婊子、嫖客與潛在謀殺犯。不談諸多顯眼的技術瑕疵(如沙發一腳撞斷後莫名在下一顆鏡頭被接回、人物對話出現明顯跳接),外勞幻夢、外勞現實、台北市亂象的三層跌宕賦予《台北星期天》面對移工問題時的可貴輕盈感,是何蔚庭當年構築得最勾人的創意,叫人難忘那些作為幻想與現實中介道具的中景沙發全家福。

中景的沙發全家福,在《台北星期天》如何強化主客逆位的主題呢?總地說,那張紅色皮沙發弭平鴻溝、反讓都會客座的外勞處境成為敘事引導者的方式,不只是它成為假想遊戲(make-believe play)中的道具(prop),也包含以沙發為主體的幻想在電影中是漸進成形、漸進融於現實,最終達成高不成(台北生活)低不就(外勞幻夢)的妥協。
沙發美夢第一次出現在外勞馬諾奧與達多在天台聊天時,德布西(Claude Debussy)的《月光》倏地作為非劇情音源插入,攝影機順勢向旁一鏡搖入馬諾奧的幻想:與情人在紅色沙發上歡愛。確立《月光》與人物動機的連結後,沙發美夢第二次現形緣起於一張牆上巨大的家具廣告;此處的影像處理是,《月光》響起,鏡頭小小移焦讓觀眾注意力由馬諾奧和達多看海報的身姿移到海報內容,接著分次剪入表徵兩人幻想的沙發平面照。經過台北週末的一日折騰,沙發夢收束於一個不那麼美好、同等虛假,卻於現實酸苦妝點下更動人的版本:沒有家庭,無關情人,更不可能有德布西,但兩個漢子於夢中,尚能倚著沙發飄浪北市、高歌一曲。這個由現實掙扎邁向妥協的過程,甚至可能驅動著在電影工作者意圖之外的形式旨趣、昇華了電影最後連第三版夢境都要敲碎的無情,亦即平面空間中物件對稱、置中的視覺意義,在電影中總悄悄經歷著正面到負面的轉換:由平面空間超脫現實的美好幻想,一路駛向社會位置被線條框住的無趣人生。
這個未發展完全的形式旨趣,在自行援引《台北星期天》的《青春弒戀》中大多佚失了。我樂於提醒諸位,直面描繪、平面空間突出的構圖方法,一方面乃常見的全家福照拍法,卻又可以是色情網站上偷拍、自拍影片或類 POV(Point of View,主觀鏡頭)影像撩撥觀者色欲的速食技巧;這個從全家福照到青少年淫照的轉向,似乎也總結了何蔚庭此次對出道長片的回望。《青春弒戀》中景平面空間框限出的情慾流動作為攝影眼評選出的生活奇觀,輔以漶染畫外的淫語、隱現帘後的裸胴、敗露物前的慾色,凡此種種,無一不屬有遮比沒遮更情色的官能性淫巧。

若有所謂的楊德昌電影遺韻……
持平論,此處稱為「淫巧」的技術,如非太重的官能性遮蔽住創作者眼界,仍在《青春弒戀》少少瞬間翩出幾許楊德昌電影的遺韻。
舉《恐怖份子》運用平面空間的鏡頭為例。馬邵君飾演的攝影師小強於電影初登場時是畫外,觀眾透過快門按鍵聲與警員老顧伸手指向鏡頭的動作推敲出照相人存在,下顆鏡頭小強才現身。這組鏡頭的奧秘是,透過撤掉正反拍的「起手式」來混淆鏡頭主客觀,也就是,不讓觀眾預期接下來看到的鏡頭可能代表某物視線,然後在該鏡頭進行到尾聲時,鏡頭中主物件作出指認動作,剪接到下個鏡頭,才透露上顆鏡頭可能是人物的主觀視點。這技巧在電影中早早出現來建立觀眾的防備心,使《恐怖份子》諸多鏡頭充滿曖昧——明明那麼冷淡的鏡位,但下一刻這「真相的無情」,是否會被剪輯揭露為他人的主觀幻想呢?遂叫觀眾同劇中諸人一般深感訛言叢聚,陷入無話可說可信的都會焦慮。
《青春弒戀》有一對鏡頭,似有觸到信任感崩塌的惶然一瞬:便利商店中的 Monica 身後突然出現郭明亮,二人擁抱,緊跟著的反打鏡讓郭明亮再度現身,讓前顆鏡頭僅為人物妄念的唯一可能頓時昭然,因為觀眾預期同個人物不會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雄性淫窺健在,然而至少,窺視快感以編排過的調度相對冷靜地投射至觀者對畫面預期的落空中,因為在第一顆鏡頭,柱子擋住 Monica 右側,明亮自柱後現身擁抱 Monica 的行動所召出的驚悚感,不光是明亮自想不到的藏匿空間現身,也因為觀眾對故事前情的認知倏地面臨挑戰:Monica 不該認識郭明亮才對。
若何蔚庭能向他處延伸這組鏡頭的功效並一致地複製它,誠實說,《青春弒戀》至少會是冒犯但還算好看的後設情色片。我不免惡毒地想,是否是那層薄薄的社福意識遏止了《青春弒戀》擴大利用錯誤的Z世代形象,以至於我與三五好友錯失一個重大可能性,亦即在某個微醺、失神的週末一起陶然於一部更純粹、更認真以新電影為題材的諧仿春宮或精緻的情色片?畢竟,我自始自終都不買帳藍祖蔚所言「何蔚庭將流行現象反推個人處境的現象學」。稍稍浸淫流行文化的觀眾,無一不能指出這片完全沒有什麼現象:Monica 那支謎片在現實不會走紅、郭明亮玩的暴力電玩更不會有人玩。它不大可靠的田調讓它無論如何構不成現象,也當不成以假亂真的春宮片,但這贗品感倒歪打正著地強化了諧仿春宮片特性,適於以虛假的現象展示做無止盡的主觀窺淫誘導。

對讀契訶夫《海鷗》的詮釋可能
形式談多、車速過快,作為收尾,淺談故事上的疑惑。《青春弒戀》多處置入契訶夫的《海鷗》,這與它自命為《恐怖份子》(Terrorizers)同樣都不叫我信服,我亦無願一坑一鏟沙地出力填梗,但還是粗率作一推斷,供好事者自行校驗:何蔚庭極可能是看上這齣名劇突出的潛台詞和強烈的後設劇場(metatheatrical)性質,再據此將《海鷗》中失意女演員妮娜與失意劇作家康斯坦丁的遭遇移花接木上近年的隨機殺人新聞,也才有片中郭明亮與Monica的交流模式:缺乏原生家庭關愛的康斯坦丁,其殺海鷗贈與妮娜所象徵的夢想失落,以及求愛妮娜不成就自殺的莽魯忿懣,一旦將動機修改到僅剩「我為了交女友做的演出/創作」,得到的幾乎就是《青春弒戀》。
契訶夫甚至能代為解密另一困惑,那就是片名的「青春」究竟所指為何?過往的青春片名導相米慎二(乃至於其後的岩井俊二)或約翰休斯(John Hughes)的青春大都限於刻劃校園男女的成長危機,相米慎二酷愛耽美與死亡,約翰休斯中意博取青年認同,但都符合台灣普羅觀眾對青春校園電影或青少年電影的既定印象。然而契訶夫的青春更適於當作老人眼中的青年人(Youth)而非校園學子,尤其對應到劇中老醫生多恩(Dorn)的幽嘆。這老人廣被劇評們視為部分代言契訶夫的心聲,齏志待歿表象下的他是善解情慾、流連溫柔鄉的清明浪子。那句「喔,青春,青春!」正是多恩的嗟嘆,作為故事中少數真正賞識康斯坦丁才華的長輩,因為嗅探到他對妮娜的少男思慕而發。但在此處,不可不提契訶夫另有摺入引線,也就是另一人物瑪莎聽到這句話時的反應:「無話可說時,就只會講青春。」正是透過將數種矛盾的情態並置出裂罅,既抽離又深入,既嗟嘆又貶抑,既想望又麻木,敏銳者方可覺察契訶夫劇作實以超然冷靜暴露生活中進退兩難的僵局狀態。
然而,如果契訶夫對青壯年生活的「無話可說」實則處處是話,不免要用瑪莎的台詞反詰《青春弒戀》先是情色化台北、再讓致敬對象的新電影早已悼亡數十年的鄉土老派莫名還魂救援之下,何蔚庭又說了什麼?

就這問題,我給不出答案,亦懷疑何蔚庭能否交出討喜的答卷,倒是看到柯志遠一文高捧《青春弒戀》為大人對 Z 世代倥傯族的懺悔書時深感突梯滑稽,畢竟此種「你因為空虛所以幹壞事」的邏輯嵌入家庭通俗劇框架而生的懺悔書,展現歉意的方式大抵是「大人要為你們千禧寶寶看情色片抱歉」、「大人要為你們千禧寶寶喜歡暴力電玩道歉」、「大人要為你們千禧寶寶喜歡角色扮演道歉」、「大人要為你們千禧寶寶享受性愛道歉」一類吾等收受人最想就地焚毀的類型——遑論,假設《青春弒戀》真有歉意,是以將道歉對象的謎片作致歉禮,這般無人想領受、其設計甚至早已回流當代謎片與黃本創作而成老調的爛梗。許多近日的謎片和黃本,可都是拿「因為對不起你/仰慕你/愛慕你/想認識你,所以拿以你(這個校園 A 片女神)當主角的謎片請你簽收」開局,發展成以性愛為簽名形式的 1v1 甚至 1v 多故事。
以維持《青春弒戀》的贗品特色為前提,我倒寧願 Z 世代影迷積極樂觀地把它看成摹寫《恐怖份子》、《愛情萬歲》(1994)的諧仿春宮片。說台北青年、阿宅、尼特們都是群婊子、嫖客與潛在謀殺犯固然冒犯,但點開諧仿春宮片,有時亦只是想戴上自我調侃的假面苦笑一番。尤其,當看片時嘲笑的不只是自己的興(性)趣,還是嘲笑那被迫親身示範興(性)趣的自己時,阿 Q 精神就更顯重要,或者,改稱之為「海鷗精神」——可別忘了,悲觀的契訶夫生前不遺餘力將《海鷗》與《櫻桃園》定位為喜劇。娛虐鑑賞《青春弒戀》,原來亦是修復它失敗設計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