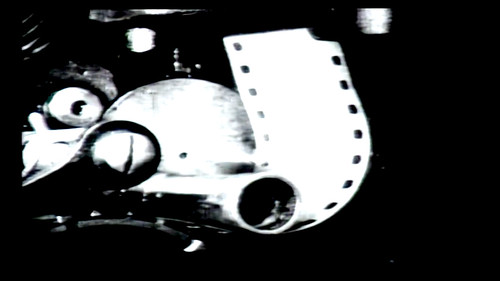高達的影像之書

王派彰與唐翊雯策展的「X+3=1:影像的削去法」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放映了高達 2018 年的《影像之書》(Le livre dˊimage)。只映一場,所以嚇得吳俊輝、林盟山、吳梓安不敢不趕去看?看得我想入非非。
(1)幾乎全部由許多著名的電影與一些你我不知的、沒看過的電影構成。我的意思是高達看過的電影遠比你我看過的多。
既然高達不必再增補「拍攝」許多影像,那麼《影像之書》的「剪輯」就顯得非常重要。這跟雷奈說到自己的電影不在於「拍攝」了「什麼」,重要的是「怎麼」「剪輯」,是相通的。
高達在使用這麼多別人的影像時,好像主要是使用「畫面」,高達加進的是「聲音」(旁白)的評述,因而另有新意。這些「聲音」並非為別人原先的「影像」服務,而是批判、甚至背離,這種「聲音」與「畫面」分分合合的辯證,又跟雷奈電影《去年在馬倫巴》與《穆里愛》以及高達以往的(或者說多少年來一貫的)「聲音」與「畫面」的實驗,都遙相呼應。
每當你我在觀賞高達擷取的別人的電影的片段而陷入(美好的?)記憶與畫面情節時,高達新加進的聲音評述其實「嚴重」干擾了你我的陶醉而頻頻被提醒我們正在看電影而不是忘情於故事中,這種「疏離」效應,也是高達受布萊希特影響的一貫作風。
(2)高達的《影像之書》擷取的別人影片片段,往往畫面失焦,色彩失散,常常並不美好。或許有點二、三十年前台灣的王墨林最討厭中產階級在固定劇院看舞台劇的舒舒服服與不食人間煙火,而把小劇場的演出拉到山崖、水邊,要觀眾在前往看戲的路途體驗一下周遭的環境。
(3)我不免想起高達與英國歌星米克.傑格合作的《同情魔鬼》(又名《一加一》),拍攝「滾石合唱團」的演唱,竟沒有任何一首歌是完整映現的。
(4)《影像之書》在擷取費里尼電影《大路》時居然「加工」讓原本正常的動態影像以slow motion樣貌映現。以往你我最詬病的台灣各電視頻道在播映寬銀幕電影時,總是把電影的左右兩側粗暴切除,只為了好讓類似正方形的電視螢幕填滿。相形之下,日本比較尊重電影的原本長寬比例,寧可讓電視畫面上、下各有黑邊。
(5)既然大多數影片的畫面都被高達搞得失焦或色彩完蛋(安哲羅普洛斯的《霧中風景》也同樣「淪陷」),那麼高達顯然不是特別菲薄費里尼的《大路》。只是,為什麼法國詩人考克多中箭的黑白片《奧菲遺言》畫面清晰、美國電影《琴俠恩仇記》(Johnny Guitar)的色彩鮮麗?莫非高達獨厚某幾部電影?微妙處,還有待王派彰指點迷津,或是央託黃建宏開釋。
(6)高達擷取這人、那人的這部、那部電影而構成「新」的章節、「新」的意涵,以我「非學院派」而又對電影外行的眼光打量,我倒覺得彷彿華人社會昔日「集句」,摘取多首別人詩、詞裡的字句,組成對聯或另一首詩、詞。
譬如「燕子歸來,還經得幾番風雨;夕陽無語,只可惜一片江山」是梁啟超集古人句;「人心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山」是胡適集古人句;「同是天涯淪落人,卿須憐我我憐卿」是我從昔日兩位詩人的名作各選一句組合成我一篇文稿的標題。
(7)影像之書有個章節用了很多篇幅談阿拉伯人(以及穆斯林)。這讓我想起雷奈 1963 電影《穆里愛》控訴法國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族群)的迫害與暴行。高達也指責過以色列多少年來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蹂躪與殘殺,以及美國不問是非總是偏袒以色列。同樣,《影像之書》也有探討共產黨的章節,既有美國恐共得濫捕濫殺共產黨員與左派人士,也不乏有些共產黨國家本身(對人民)的暴政。巴索里尼《1001夜》裡的美少男與裸男,則被高達擷取到阿拉伯的相關章節中。
(8)高達的《影像之書》在擷取這個、那個畫面時,有時候這些畫面的組合被高達剪輯得很「意識流」。譬如,尋常幼兒在地上爬行的畫面,接到雪地軍服的兒童們的爬行,再轉換到巴索里尼《索多瑪120天》許多裸體美少男美少女(被二次大戰的法西斯當成狗)集體在地上爬。如果說雷奈的《廣島之戀》、《去年在馬倫巴》與《穆里愛》以及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都是畫面極美、構圖神奇,電影如詩的「意識流」,那麼,《影像之書》的「意識流」比較像是哲學論文。
(9)早在 1965 年高達的《狂人比埃洛》時期,他就認為「Velasquez 50 歲起就不再畫精確的物體了。他要畫的是,在精確的物體與精確的物體之間的那一切東西。」你我如果緊抓住這番話,將不會被《影像之書》嚇到,甚至會以為看懂了《影像之書》。當然這種「懂」,是永遠比不上王派彰的啊!
(10)看《影像之書》有些遺憾。《影像之書》映現歐弗斯(Max Ophuls)《歡愉》(Le Plaisir)裡的法國美女達妮葉.達麗尤(Danielle Darrieux)的身影,這位法國著名演員 D. D. 在法國、美國、英國、日本家喻戶曉,近期以高齡 100 殞逝,台灣竟少有人知。導演歐弗斯的非比等閒,也只有電影學者肥內(王志欽)特別珍惜。
(11)另外,本片的法語旁白中譯,知道把象徵派詩人 Arthur Rimbaud 譯成「韓波」,卻不懂把作家 André Malraux 譯成通用的「馬候」或「馬勒侯」,而搞出什麼非驢非馬的「馬爾羅」!台灣文化評論界不是早就把 Jacques Derrida 譯成「德希達」了嗎?
(12)《影像之書》高達加進了根手指(以及一雙手)的畫面,王派彰已有開釋。■